近期活动
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《檀岛花事》的报导
《燕园草木补》出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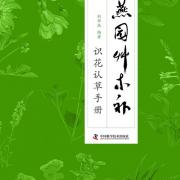
刘华杰编著《燕园草木补》2015年11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。
公众不应当放弃自己感受、了解大自然的权利
《中国教育报》,2016.01.02,4版
问:缇妮(博物爱好者)
答:刘华杰(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)
问:近十年来您一直倡导博物文化、博物生存、博物人生,并且从知、行以及传播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与实践。请您谈谈博物的文化精髓是什么?
答:博物学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分支。博物学在各国都有悠久的历史,从回溯的角度看,博物中也必然涉及大量可靠的知识,因此人们习惯于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 博物,说博物与科学有交集。这当然是有道理的,但是,博物与科学都不是对方的真子集。我们今日想复兴博物学,并非只是在某个学科的意义上复兴它。
一般而言,博物学的魅力在于它不同于当今的自然科学。在追求上、方式方法上、职业要求上都不同。但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人与自然世界打交道的途径。在现代社 会中,绝大多数人放弃了个体感觉、认知大自然的本能、能力,把它交给了科学家,托付给了权威机构。这样做的前提假定是:它是理性的、经济的。科学家更擅长 做这些,用不着每个人来操劳,自己来做反而不精确、不深刻。其实这只有部分道理。公众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实践?是否考虑过放弃的代价有多大?
如今,博物学从业者仍然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科学家中的博物学家,一类是普通百姓中的博物爱好者。我以为,要复兴博物学,主要是针对后者而言的,即恢复公众的博物学,让普罗大众的生活更充实、美好。
恢复的用意是什么?为了我们的生活世界!“生活世界”是相对于“科学世界”的现象学术语,也可以在日常语言的层面理解。科学世界是科学家发明的、为描述生 活世界而建构出来的、化简的、模型化的世界图景,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伽利略、笛卡儿。而生活世界是真实可感的、不可再后退的、唯一真实的世界,百姓对此是 熟悉的。科学世界要为生活世界服务。这是个普通的要求,却时常被忘记。有些科技盲目发展,不能真正为凡人的日常生活服务而用于歪门邪道,如榨取剩余价值、 欺负弱小、破坏大自然等。
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哪个更真实?受过教育的人容易误以为科学世界更真实,其实这是错误的、本末倒置的。现象学就是要把颠倒的恢复过来。
发展公众博物学有助于百姓切实了解自己的周围世界,遇事不是仅仅相信他人怎么说、书上怎么说,要自己切实感受事情是怎样的,自己作出判断。注意,我用了“感受”而不是“推理”。
问:博物学意味着什么?它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着什么角色?
答: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,博物学包含人这个物种了解自然世界、求得生存的基本知识、能力和技巧。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博物学,20世纪以来,博物学衰落了。表 现之一是,个体不了解家乡和社区,不了解天气和空气,不了解土地、山脉和河流,不知道牛奶、蔬菜从哪里来、怎样生产出来。博物学衰落带来的后果,是人类对 大自然变得麻木、没有敬畏感,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也变得无所谓。人类越来越习惯于人工环境,自然生存能力降低。
如今人类的发展遇到了重大问题。十几年前北京人认为大风是环境恶劣的罪魁,而如今大风是吹散雾霾的功臣!风并没有怎么变,变的是人,是人的认知。谁在污染 首都北京?现状是在什么名义下形成的?人们不愿意承认或者根本看不见基本的因果链条。现代性的逻辑只关心局部和局部外推,只在线性区附近工作,而世界本质 是复杂的、非线性的。博物学根本不采用复杂的数理模型,它沿袭和传承传统,相信基本常识和感觉,不用强力快速改造世界。博物致知、博物人生,尊重二分法中 弱、慢、柔的一面,对科学结论持适当的怀疑态度。在科技的时代,公众如何看待科学结论?这涉及科学传播的理念、目标。一种极端是完全听专家的;另一种极端 是完全不听专家的。这两个极端都不是现在学界所推荐的和百姓所期望的。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只有对话的出路,公众有权利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判断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:公众凭借哪些资源来判断?公众作决策的基础理论上有三个方面:(1)科技方面;(2)逻辑推理;(3)自己的博物实践。逻辑推理实际上在 科学和博物学中都有,因此以上三个方面可进一步简并为两个渠道:(1)科技渠道;(2)个人博物渠道。至此,读者可能明白,我所讲的博物学意味着什么。它 当然很重要,它将参与形成公民自己的判断力。百姓多一些博物知识,就能多一些规避风险、灾难的主动性。
问:您的《博物自在》作为博物学的入门书,向我们展示了博物的西方传统和东方传统,同样展示了迷人而有趣的历史,也拓展了我们对博物的认识视野。请您归纳一下,东方的博物与西方的博物有什么不同?
答:我的《博物人生》《博物自在》《博物致知》三本书展示了东西方博物学的某些侧面。实际上,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博物学都有自己的特色,有强烈的“地方性知 识”或“本土知识”(indigenous knowledge)的特点,都非常有趣、有价值,但目前都在快速消失。相同的方面是,都是应对自己的小环境的产物,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,都是适应于本地 的。这种带有地方特点的知识、方法或者生存智慧是经过反复检验的,它们没有幻想成为普适的、推向全球的知识、价值观。因此,差别也是巨大的、多方面的。中 国古代的博物学与我们的古代哲学一致,比较强调天人合一,没有把自然推向纯对象的地位,即客观性不够。这是缺点也是优点。在评价各地的博物学时,要强调文 化相对主义,而不能用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。
问:博物作为古老的学科,其实渗透到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,比如绘画,同时也发展和培育了很多艺术门类,但那些东西似乎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。您今天倡导复兴博物,意义在哪里?您觉得我们今天的复兴与古人的博物有何不同?
答:在现实中,我经常强调的反而是博物学的无用性,用梅特林克的话讲,是“无用而美好”。如今许多事情的弊病恰好在于,太强调“有用”。对此,博物学走的 是正相反的路子。我们百姓的生活中充满了大量无用而美好的事情,修炼博物学能够为自己做这类事情辩护。建筑包括有用的方面和无用的方面,太在乎有用,就堆 出了无数十分难看的城市建筑。我们在博物学上“浪费”时间,可以获得好心情,同时又了解到周围的动物、植物、生态,这难道不好吗?没有人敢断然否定。但一 定有一堆人等着说:针对其目标,有更高效的达成办法,比如有科学的办法,因而用不着抬出已经过时的博物学!听起来似乎有道理。其实完全无理。在现代社会 中,人的欲望持续膨胀,驱使现代性的车轮越转越快、列车越跑越快,风险和不适也越来越严重。博物学虽然强度不大,但它可持续,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体验。
如今复兴博物学,理论上与古人没有太大差异。古人能感受“杨柳依依,雨雪霏霏”,我们也能。他们能做许多“无用”的事,我们更能。他们博物,适应于环境,不搞扩张,按理说我们也能。要讲不同,今人需要选择,需要认同博物学才能过博物人生。
问:听说北大附中等学校一直致力于学生的博物教育,您也不断到学校作讲座,您认为我们的博物教育应该怎样进行和开展?
答:博物教育主要是一种自我教育,这是它不同于“自然教育”之处,但自修也需要引导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办《博物》杂志,北大附中开设博物课,还有人受我的 影响走上博物之路。每个人都能作出自己有价值的努力。许多博物学家、自然教育家做了非常棒的传播工作。对我而言,我首先要测试自己能否过博物人生,即 living as a naturalist,在此过程中有怎样的收获和损失。多年测试的结果是:通过。也就是说,我能够拿出足够的时间来博物,在此过程中能够具体了解我周围的 草木,到一个陌生地后能迅速了解周围的植物。前者以《燕园草木补》《天涯芳草》为证,后者以《檀岛花事》为证。我甚至能够看到科学家不曾看到的许多现象, 发现被常人忽略的许多美好。
《博物人生》第2版出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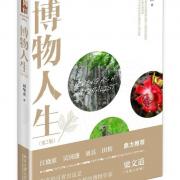
《博物人生》第1版2012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,平装。修订后现在出了第2版,精装。

